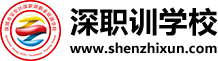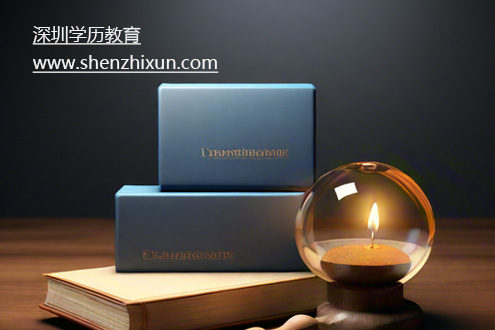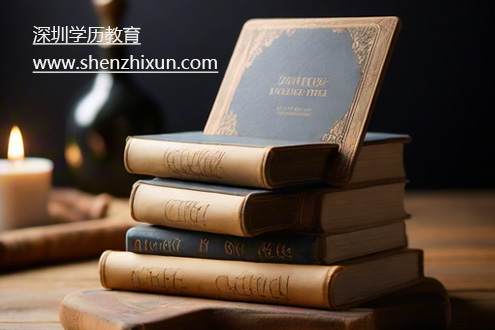电大与网络教育:虚幻与真实的教育困境(电大和网络教育哪个好)
一、纸糊的学堂与虚幻的光
我这人本不擅说教,然见近来街巷热议电大与网络教育优劣,倒像茶馆里争辩咸豆浆与甜粽子哪个正宗,实在引人发噱。忽而想起乡下老宅檐角的蛛网,挂些露水便摇身作珍珠帘子,可见世人总爱将虚幌子捧成真道理。
八十年代的电大,好比用粗瓷碗盛着龙井茶。工人下了流水线,农民歇了锄头,守着老式收音机听讲学,活似庙里的泥菩萨听和尚念经。那课本油印得模糊,倒像是浸了雨水的手抄本,可偏有人将它视作通天梯,踩着铁皮铅笔盒往"知识分子"堆里爬。
如今的网络学堂,倒换了西洋景。电脑屏里教书先生的面孔,分明是像素拼成的画像,却比城隍庙的判官更教人敬畏。学生在这头的摄像头前正襟危坐,倒像戏台上的木偶,线绳却牵在屏幕后的云服务器手里。
二、孔乙己的茴香豆与键盘上的回车键
咸亨酒店里孔乙己教人写"茴"字,现今网络学堂里学生抄代码,倒是一脉相承的戏码。只见那课程视频放得热闹,学生在评论区敲着"666",仿佛捧场看大戏。某日见隔壁阿三在直播间答题,手机屏幕的光映在油渍斑斑的外卖服上,倒像月夜里的萤火虫歇在煤堆里。
电大当年的考试,监考官查得严,纸条藏在钢笔帽里,像是往粮仓偷米的耗子。如今网上考试,人脸识别瞪着眼,倒像阎罗殿的照妖镜。可那些考试代过的小广告,在电线杆上贴得比治梅毒的偏方还密,活生生一出新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。
有学员将课程进度条拖到底,证书打印得比灶王爷的年画还鲜艳。这样的学问,怕是要像孔乙己的长衫,中看不中用,遇着事连个"茴"字写法都解不得。
三、阿Q的辫子与新时代的文凭
未庄人见留洋学生便矮三分,今人见着名校证书就软了膝盖,这奴性倒是一脉相承。电大文凭装在玻璃框里,供在客厅当辟邪符;网络教育的电子证书存在手机,如同随身携带护身咒。二者殊途同归,不过是要在旁人的眼神里讨口饭吃。
见过卖煎饼的王二,白日里在电大学会计,夜里算账却总差三毛钱。又见写字楼里的李小姐,揣着网络营销证书,在淘宝刷单群当军师。这让我想起赵太爷说阿Q:"你也配姓赵?"如今的用人单位何尝不是在文凭上画圈,将活人分成了三六九等。
那课程表安排得再精巧,若教不出真本事,不过是给纸人画眉眼。电大也好,网教也罢,若只顾着在证书上贴金,倒不如祥林嫂捐的门槛,终究救不得命。
四、未庄夜话与赛博课堂
深秋夜半,未庄的油灯下学子抄笔记,与今日台灯前刷网课的年轻人,隔着百年时光对望。当年用钢笔尖蘸着蓝墨水写"之无",如今用触控笔在平板上画思维导图,工具换了模样,求知的饥渴倒还似月光般清明。
常见菜市场的张婶,趁着卖菜的间隙看会计网课,手机上沾着韭菜叶;也见工地老刘戴着安全盔听电大讲座,安全绳上别着笔记本。这样的学习,虽不如翰林院风雅,倒比茶馆里说书的更动人心肠。
可见学堂好坏本不在屋顶高矮,教书先生是血肉之躯还是数字幻影。就像药引子要用原配蟋蟀,治病还需对症下药。求实用者选电大,图便利者取网教,各得其所便是佳话,何必学九斤老太念叨一代不如一代?
五、新式药方与陈年痼疾
有学究痛心疾首,说网络教育让学问成了流水线上的罐头。这话倒让我想起当年骂火车会惊动祖坟的遗老。《狂人日记》里的仁义道德,换个包装继续在新时代招摇撞骗。
某技术学院的电大生,将机床操作手册背得烂熟;网络课堂里的编程小子,在开源社区与人论剑。这样的场景,倒比四书五经堆里出腐儒可喜得多。只是那些只顾混文凭的,像是给草人披上锦绣袍,风雨一来就露出原形。
夜深想起闰土说的:"读书人真能懂我们挖蚯蚓的苦么?"无论是电大的广播还是网课的视频链接,若能打开新天地的窗,便值得喝彩。怕只怕把教育当作变戏法,最终变出满街的孔乙己,顶着学士帽说回字的四种写法。
声明: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,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,均为采集网络资源。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,可联系本站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