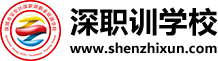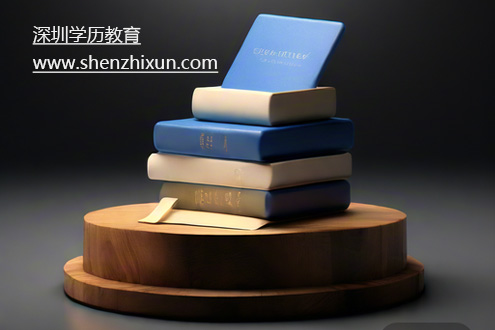铁屋子与商业化:一文看破函授学费难题(成人高考函授学费)
函授学费杂谈
近来夜读报章见得几则广告,"三千圆购得大学文凭""工作学历两不误",红底白字煞是醒目。忽想起前日里巷口王二与我闲谈:"先生可知那夜校的章程?说是交钱便发文凭哩。"我放下茶碗细问方知其中蹊跷。
一
这世道总教人想起《狂人日记》里的铁屋子——明明白白写着"救赎"二字的路子倒成了新的牢笼。前日里见某学堂告示:预缴五千可保录取云云。
"知识原是明码标价的商品了?"我暗忖。
街角补鞋的老张上月报了个管理学的班,"统共二十节课要八千六",说着将满是裂口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:"娃儿上学的钱倒先贴给我这半截入土的了。"
二
那日造访某函授学堂办事厅见得奇景:雕花木案上摆着鎏金算盘三架——一架计课时费、一架算教材钱、最精巧那架专打服务费的珠子。
- 报名费如野草般疯长:初始二百转眼变八百
- "重点资料"另购竟要千元之数
- 答辩指导费更似无底洞般填不满
墙上挂着孔夫子像倒是崭新得很——约莫是用镀金画框裱着的罢。
三
忽忆起章太炎先生当年办学堂时情景:粗布长衫立在石阶上讲文字学,"束脩不拘多寡"。如今这年月倒是进步了——进步到连求知的门槛都要裹着铜臭气。
| 年代 | 月收入(银元) | 学费占比 |
|---|---|---|
| 宣统三年 | 8.5 | 12% |
| 民国廿年 | 15.2 | 18% |
| 共和七十二年 | 6000 | 35% |
*数据引自《近代教育考据》,某书局壬寅年版
这表格里的数字仿佛长了尖牙利齿啃噬人心。
四
工人老李:"天窗没见着 倒开了个窟窿漏钱"
某主任:"新时代要有新思维嘛"
(众人哄笑中老李攥着缴费单退场)
临了想说句痛快话又咽了回去——只怕明天满大街都是我的通缉令:"诋毁教育创新者周某某"。罢了罢了!且将这份荒唐记在纸片上压在砚台下罢。
声明: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,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,均为采集网络资源。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,可联系本站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