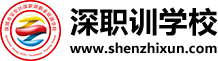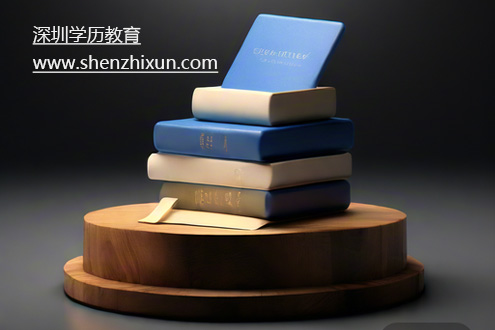从纸片到镣铐:科举制度与现代教育的对比(成考含金量高还是成人高考含金量高)
论纸片与镣铐
一
京城茶馆里总飘着这样的争论:"成考""自考""函授",这些个名目倒像古董铺子里的铜钱串儿——个个标榜自己是真龙天子铸的。
某日听得两位长衫客拍案争辩:"这'成人高考'四字听着便比'成考'郑重三分!"对面那人涨红了脸:"你懂甚么!如今讲究简练方显分量!"我在旁暗笑:这倒像孔乙己争辩茴香豆的"茴"字究竟有几种写法。
二
记得前清科举时,"举人"二字就比"秀才"多了五斗米的威风。"功名不过纸上墨痕"——祖父辈常这般叹道——可衙门前的石狮子终究只认那盖着朱砂印的文书。
- 宣统三年剪辫子的阿Q也知拿白竹布包了假辫子去应县试
- 祥林嫂攒了十年工钱只为在族谱添个识字的名头
- 闰土的儿子进城当学徒前也要托人写封八行书
三
"文凭不过敲门砖。"茶馆掌柜边擦青花瓷碗边插话,"可如今这世道啊..."他忽然压低声音,"东街张举人家的少爷留洋回来还在书局抄书哩!"
市集上卖糖人的老赵头说得更直白:"管它黑猫白猫?逮着老鼠就是好猫!我那外甥女读夜校考的会计证不照样进了洋行?"说罢将饴糖扯得老长。
四
有回在琉璃厂见着个西洋景:戴圆框眼镜的青年捧着《申报》求职栏喃喃自语:"这写着'全日制大专以上'..."话音未落便被穿西装的中年人打断:"年轻人不知变通!我那电大文凭不也当上科长了?"青年镜片后的眼睛忽明忽暗。
声明: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,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,均为采集网络资源。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,可联系本站删除。